编者按
《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2022年发布的优秀文章即将结集出版,敬请期待!
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8篇文章,围绕《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一书展开的评论与思考,联系当前有关国际秩序转型的议题,从“自由国际秩序”的理论基础与发展源流反思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制度化国际秩序”的特征、贡献与局限性。

本文作者:赖永祯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博士研究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战略青年
在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革之后,新兴的主导大国如何选择塑造新的国际秩序?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里在其著作《大战胜利之后》中探讨了这一问题。该书于2001年出版,迄今已二十余年,但本书所讨论的有关新兴大国转型时期塑造国际秩序的理论主题并未过时。联系该书出版的特定现实背景,时值美国的全球霸权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时期,美国国内面临“9·11”事件的冲击以及外交政策朝单边主义方向的转变,作为“自由制度主义”代表学者之一的伊肯伯里对当时的美国应如何继续维持霸权秩序提出自己的理解。回望“单极时代”的美国如何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经验,并从中理解其逻辑与历史的局限性,对于理解当下大国博弈时期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和潜在国际秩序重塑,亦有重要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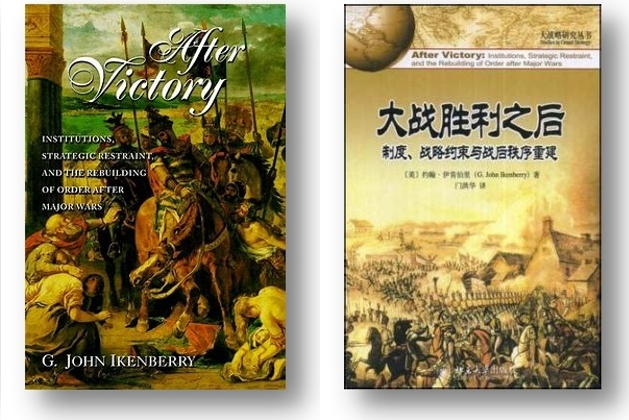
《大战胜利之后》著作与中文版译著封面
“胜利之后”的大国:以制度求霸权
在伊肯伯里的论述中,维也纳体系建立的1815年、一战后的1919年、二战后的1945年与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转型的四个重要案例,是国际战争结束后新国际秩序重塑的关键时刻:主导大国可以选择运用自身实力自主决定战后秩序,形成所谓帝国式的统治权,或者选择回到孤立主义方式、放弃建立新国际秩序,或者将自身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制度化国际秩序。
而第三种政策选择意味着国际秩序存在着向类似国内“制度化”秩序转型的可能性。同时,国际秩序自1815年以来呈现向制度化转型的趋势,即从19世纪的“均势”国际秩序向制度化的“宪制型”(constitutional)国际秩序转型。对此,伊肯伯里提出产生这一缓慢演进趋势的两个原因:一是战后主导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二是参与国际秩序设计的政体类型[1]。从秩序的概念层面理解,以上两个原因论述也间接对应了国内秩序经典定义中“对暴力的合法垄断”中“垄断”与“合法性”两个方面。就战后主导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而言,主导国家的霸权地位意味着主导国能够通过国际制度将其他国家“锁定”在符合前者利益的轨道上,并通过一定的“自我约束”来保证国际秩序的运行;同时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相比于被领导国采取帝国式的统治或被“抛弃”,选择加入主导国家的国际制度安排也符合其利益。这一类型的国际秩序以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为代表。同时,伊肯伯里认为,如果参与国际秩序的国家多为“民主国家”,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体属性使其更加倾向于透明化的国际制度约束,故而更能够促进国际秩序的运行[2]。
进一步理解可以发现,在伊肯伯里的逻辑中,主导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和其自身政策选择这一组变量可以解释国际制度塑造秩序的起源逻辑。如果国家间实力对比无法出现单一大国的主导地位,就意味着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方面通过制度安排令其他国家服从于单一大国的领导,从而形成事实上通过“均势”维持下的秩序(例如1815年后的维也纳体系)。
另一方面,即使在实力对比合适的结构环境下,如果主导国无意愿建立国际秩序,那么“宪制型”国际秩序仍然无法建立(以一战后美国退出国际联盟为典型)。而在霸权国际格局下,战后主导国家的政策选择也因此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重要变量。就这一点,主导大国的政策选择取决于其是否愿意做出短期内自我约束权力的“让步”来换取国际秩序的长期维持,从而通过将其他国家“锁入”国际制度的方式维系霸权的稳定,而非通过主导国家自身的物质资源[3]。从这一角度来看,单极霸权国家通过制度安排塑造国际秩序不仅体现在理念上的“进步性”,而且从维系国际秩序成本的现实角度来看,塑造国际制度也是效率相对较高的霸权模式。
“自由国际秩序”逻辑的张力
然而,伊肯伯里在有关“宪制型”国际秩序塑造的论述中,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理论与现实案例理解之间的潜在张力。如果仅从大国维系霸权成本的制度逻辑来解释国际制度秩序的有效性,则这一简约逻辑似乎能够涵盖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大国竞争问题:宪制性国际秩序有助于对体系中的行为体进行约束,同时减少领导国家因绝对实力而获得的附带收益,使得其它行为体在未来成为霸权国家将变成一个低回报的选项[4]。这种有关国际格局转变的论述部分来自作者所认为的西方国家多党制竞争实践中“多次博弈”的政治经验。而从现实政策的角度,这一论述也有助于美国在相对实力衰落的情况下“管理”潜在的新兴崛起国。
然而,这一逻辑似乎需要回答如下问题:即崛起国成为霸权国后是否还仍然会承诺尊崇原有霸权的国际秩序,而非改变国际秩序?巧合的是,虽然作者在书中并未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亦在其理论阐释中添加了“民主政体”作为制度化国际秩序形成的变量之一。对此,作者在此断言称民主政体在国内决策上的透明度偏好使得其更易受国际制度约束以及作出可信承诺[5]。姑且不谈政体论述本身的争议,倒不如说,作者也以一个委婉的“民主和平论”回答了国际制度转型下的“承诺”问题:即作为“民主政体”的弱国在国内政治规范中更加倾向于服膺主导国政治规范的“领导”,故而即使自身实力有所发展,也更加倾向于“自愿”服从霸权政治逻辑,从而不会有颠覆国际制度的意图。
另一方面,通过在国际制度中培育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国家,从而巩固现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减少国际制度替代方案的吸引力。但这一论述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则是,所有参与国家不仅在功能和效用上接纳,而且在规范层面上认可“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从而使得“自由国际秩序”下的崛起国不会在霸权转移后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
从美国外交实践的角度,迄今为止的国际秩序也远未达到伊肯伯里所设想的“宪制秩序”。例如他认为,二战后美国主导以联合国、北约和自由贸易体系为中心的国际制度是“宪制性”国际秩序的体现[6]。这一说法虽然突出了1945年后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霸权的兴起以及美国外交政策从孤立主义向塑造国际秩序的转变,但从全球层面来看,也相对忽视了苏联在二战后作为同时兴起的霸权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塑造作用。虽然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安排将大部分国家都纳入其中,并部分建立了大国主导下缓和国际冲突的制度形态,但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设想的联合国“四警察”为中心并将其他国家“锁入”的模式,顷刻就被两极格局对峙的“冷战均势”所取代。
从这一角度来看,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也仅仅称得上是全球范围的“均势”秩序与各自阵营内部的部分制度化秩序的混合物。而冷战期间两极霸权的地缘竞争冲突烈度甚至远甚19世纪均势格局的秩序(以殖民体系扩张作为缓和大国均势秩序的代价),远非维系国际格局稳定的“宪制”秩序安排。相反,非西方世界的安全关系反而成为霸权国家相互竞争的平台,而远未被直接地纳入既定国际制度的框架中,其在部分区域(例如东亚地区)的影响甚至延续至在冷战后的当今世界。
此外,政体逻辑作为维持宪制性国际秩序的因素也部分解释了美国在冷战结束后积极在原苏东地区扩展国际制度的行为,但是这一论述中也相对淡化了试图塑造国际秩序而进行规范输出的成本。例如,伊肯伯里在其书中提到,美国在安全上支持北约“东扩”的缘由即试图在原苏联东欧地区通过“锁入”东欧国家来拓展单极国际秩序:为东欧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增强北约的凝聚力和战略纵深、推动东欧国家的国内改革[7];以及推动建立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秩序,推动成员国实施自由贸易改革并让渡部分经济主权。
但是,由单极霸权塑造国际秩序时造成的“政体偏见”却同时也在持续地造成地区动荡:虽然单极国家从霸权维持的成本角度,并不会完全意义上地选择帝国式的“统治”(dominate)道路,但仍然会根据政体逻辑选择性地仅将部分国家纳入国际制度,而将另一部分国家有意排除在霸权创立的国际制度之外,由此产生新的国际冲突。从小布什时期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论述,再到近年来乌克兰试图加入北约引发美俄关系的紧张与不信任,以及中国崛起与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试图使中国“脱钩”于现行国际制度之外的企图,均反映出美国霸权下国际秩序预设的“自由制度中性论”和其在面对国际政治多元性之间的矛盾。而现行国际制度在表面的“制度中性”背后的霸权逻辑则是引发持续国际动荡的重要渊源。
回到历史还是创造未来?
相较于历史上的均势和帝国式霸权,伊肯伯里所言的制度化国际秩序突出霸权国家通过自我约束换取其他国家对霸权秩序的认可,以减少霸权本身短期收益的方式获得长期存续,这一原本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限制霸权转移时冲突的意图,具有其历史的“进步”属性。事实上,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后的崛起,恰好是自由制度主义所体现的一大“成功”。然而吊诡的是,中国在“自由国际秩序”框架下的崛起,却使美国视之为担忧霸权地位衰落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当前中美互动进程来看,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虽然表面上反映了霸权转移后新兴大国维系现行国际秩序的“承诺”难题,但归根结底则是美国在创制“自由国际秩序”时试图对其他国家输出合法性观念的意图与多元国际政治现实的冲突。
如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所言,既有的历史经验表明,建立国际秩序,需要确立秩序观的一致战略,并将不同地区的秩序相互联系起来[8]:这其中包括21世纪初的“自由国际秩序”向后苏联地区和中国等非西方世界扩展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一度成为“八国集团”成员为标志)部分巩固了自由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但是从非西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加入国际秩序更多的是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发展战略选择,而并非“服从”乃至“锁入”于霸权国际秩序的规范安排。
事实上,伊肯伯里的论述也间接承认了国际制度的“非中性”假定,即维持需要“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共识来维系,否则国际秩序在霸权转移后仍然会面临不确定性。但是,伊肯伯里在本书中并未强调的是,这种需要建立在塑造共同国内政治规范,以培植既得利益成员国方式来维护的国际秩序本身也在不可避免地消耗霸权成本。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反映出在美国相对实力衰落背景下,美国国内政治中存在试图以放弃部分国际制度承诺,回归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本的外交政策取向。而另一方面,以霸权领导为基础输出国内政治规范的方式,本身也同时在其他国家当中侵蚀霸权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这也导致近年来作为体系内新兴和崛起国家通过部分重塑国际制度以“抵消”霸权国家的影响力,以及地缘政治现象的回归(如乌克兰危机)。对此,米尔斯海默在《大幻想》中则直接指出国际秩序中行为体的非中性特征:国家行为体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合法性而得以存续,而自由国际秩序的推广则难以避免冲突[9]。
也就是说,除了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之外,不同国家行为体间对国际秩序与运行规则的共识与认可度也是影响国际秩序演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国际关系现有的主要理论对此提出了不同但都趋向于审慎悲观化的理解:米尔斯海默侧重强调民族主义多元现实下始终存在的国际秩序合法性问题,使得自由主义国家仍然难以摆脱“均势”逻辑。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突出国际制度对于约束成员国的作用,但是制度仍然依赖于国家间对于国际规范的集体共识预期。但是,当这种“集体共识”离不开霸权国输出自身规范塑造本国在国际体系的“镜像”时,则不可避免会产生霸权扩张问题。
对此,相比于为有限的现代国际体系历史经验所困,在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重塑一个对不同政治文明都具备包容性、开放性和参与性的国际秩序,仍有赖于各大国的自身抉择。在特定的权力结构下,国际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如自由制度主义所主张的对自身的物质权力进行自我克制,同时也更需要在处理不同政治文明之间“合法性”观念上实现自我克制;此外,大国是否能从克制单方面凭借自身优势“锁入”乃至“改造”他国来维系国际秩序,进而允许不同国家共同参与塑造国际秩序共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即使是一个更为包容的国际秩序的实现与存续,仍然取决于新兴大国自身的行为所体现的可信承诺特征。换句话说,未来的大国政治是将重复历史的“悲剧”,还是开创潜在的“可能”,都取决于主导国家在权力转移的“关键时刻”处理实力与观念的“双重克制”方式。对于当前大国博弈中的新兴崛起国家而言,如何避免重新踏入霸权国家塑造国际秩序的历史牢笼,不啻为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现实议题。
编:闫咏琪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美]约翰·伊肯伯里著,门洪华译:《大战胜利之后:制度、战略约束与战后秩序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71页。
[2] 同上,第67-70页。
[3] 同上,第47-51页。
[4] 同上,第31页。
[5] 同上,第68-70页。
[6] 同上,第193页。
[7] 同上,第217-218页。
[8]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86-487页。
[9]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李泽译,刘丰校:《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