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目前CISS正对接出版社,将2022年发布的优秀文章结集出版,敬请期待。
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6篇文章,围绕《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一书展开评述与思考,从“非主流”理论出发,反思美国发起价值观宣传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逻辑与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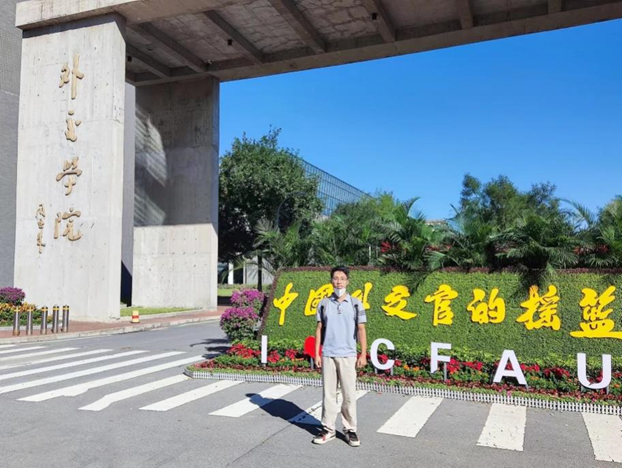
本文作者:朱翊民,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
自1998年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 Keck)与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以下简称《活动家》)出版以来,迄今已有近25年光阴。该书不仅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建构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更是社会运动、人权研究、环境政治、妇女权利等领域不可多得的一部作品。在不断有学者直呼“国际关系理论走向终结”的当下,[1]重新反思这部诞生于“主流”理论论战时期的“非主流”研究,或能为进一步观察国际关系学的相关现象、增进学理研究有所裨益。
全书介绍与理论逻辑
《活动家》一书共六章。其中,第一章主要在学理层面介绍有关跨国倡议网络的理论框架及其分析机制。在作者眼中,跨国倡议网络具有三种特征,分别是“跨国性”“倡议性”与“网络特征”,具体则指这些行为体主要从事跨国活动;它们的形成是为了提倡某种视野、道德观念和规范;同时,网络中的群体之间存在着正式或非正式的紧密联系,是一种“知识共同体”构成的网络。在论述其生成时,作者提出了跨国倡议网络的“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 of influence)”,指出正是因为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国内非政府组织只能通过绕过国家诉求国际行为体以对国家施压的方式达成自身目的。
就其作用来看,作者认为跨国倡议网络利用四种策略施加自身影响,分别为信息政治(揭露、报道、曝光)、象征政治(框定、再阐释、利用舆论)、杠杆政治(物质杠杆、道德杠杆)与责任政治(说服、承诺)。继而,作者进一步分析,满足合作需要何种条件?作者较笼统地指出,议题特性、包括作为施动者的跨国倡议网络与作为目标的国家等因素都会影响具体的成效。
在这一总体框架基础上,作者在第二章介绍了跨国倡议网络的背景与历史渊源,以图在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中凸显跨国倡议网络的重要意义,具体包括1833-1865年美国与英国爆发的废除美国奴隶制运动、1888-1928年保障妇女投票权的国际投票权运动等。在全书第3-5章中,作者将理论框架融入对不同结果的案例考察中,并分别利用人权、环境保护与妇女赋权的三个个案验证其基本假设。其中,人权与妇女赋权的案例为跨国倡议网络成功施加压力并促动国家政策变更的正面案例,环境领域的案例则包含了一组存在结果差异的比较案例。最后,在全书第6章中,作者对跨国倡议网络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具有广阔前景”的若干研究议程。
理论与学科意义
《活动家》一书兼具理论意义与学科意义。一方面,在严密的章节编排下,作者在坚定维护建构主义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国际关系社会学转向的“路线图”。作者从非国家行为体的角度出发,解释了全球公民社会怎样把世界上将他们认为“好”的事务和“应该”存在的事务变成了政治现实,有力地以适当性逻辑驳斥了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逻辑,是建构主义在与理性主义展开理论论辩时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2]
另一方面,就国际关系学科史整体看,《活动家》一书对国际关系学科亦有持续的衍生性意义。其一,《活动家》全书较完整地回答了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何有的观念作用明显,有的观念收效甚微,有些观念甚至难以在国际社会中被关注?[3]作者的回答将被忽略的跨国倡议网络纳入至国际关系学分析视野中,并首次对其行动逻辑展开系统性剖析;同时,作者更以众多国际领域的社会运动为研究对象,扎根式地对一系列过去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不易解释的经验事实及其运动流变做出阐释。
其二,《活动家》丰富了新千年以来的国际关系研究学科议程。其中既包括接续其研究主体进行深入探索的“国际组织学”“非政府组织化”研究,亦囊括对规范具体议程、规范属性出发进行的衍生性尝试,还衔接研究规范扩散与规范本土化等相关文献。[4]由此观之,《活动家》的相关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并不是孤立的研究议程,其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学科具有相关性并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
逻辑限度与批判性反思
如前所述,《活动家》在理论与学科上皆占据重要地位,但囿于时代背景、范式通约等因素,《活动家》存在一定逻辑限度与理论缺憾,使其成为跨国倡议网络研究、规范研究的“中点”而非“终点”。
具体而言,一方面,《活动家》因果机制上侧重阐释,在实证性上略有缺憾。纵观全书,《活动家》尽可能以过程追踪法将多重因素导致观念传播差异化的具体因果机制呈现给读者,然而,需要反思的是,是跨国倡议网络作为主体而独立地导致这些事件发生吗?议题特征、跨国倡议网络本身与国家对规范传播差异的因果机制能否利用更加精确、可操作的指标进行衡量?目前来看,由作为自变量的跨国倡议网络行为到作为因变量的观念变革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相较于理性主义范式仍显得较弱。在全书论证中,作者难以完全排除如地方性规范、国内政治结构、国际结构与关键节点等竞争性解释的影响,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机制由此难免出现权重不一、逻辑位次较为模糊的现象。同时,自变量过多而难以统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者构建理论框架的简约性,上述存在的限度使《活动家》在方法论上具有建构主义范式中“强阐释而弱实证”的普遍局限性。[5]
《活动家》试图从“设定议程”“影响国家与国际组织的话语立场”“对制度程序的影响”“对目标行为体的影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等角度评判跨国倡议网络产生影响的几个阶段。然而,这一标准是相对静态的,作者虽然将跨国倡议网络行为的影响纳入具体进程中,但这难以回答“该影响能否具有持续性”“是否会出现观念传播在相对成功后又出现退化的情形”?并且,作者仅提供了一个所谓“成功”或“不成功”的二分式结果作为参照,对于跨国倡议网络导致不同类型结果的讨论尚缺乏,从而使对跨国倡议网络行动结果的评估存在很大主观性。
综上所述,《活动家》呼吁学界关注过去不受重视的跨国倡议网络、知识共同体、非政府组织这一支激进力量,然而,既有学界对其理论与书籍的衍生性反思尚较少,超越其理论内核与逻辑论证,或能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镜鉴。
“被忽略的他者”?非政府组织与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
从这类主体进行引申思考,从《活动家》诞生迄今的20余年内,在学理上的确不存在所谓“跨国倡议网络学”“非政府组织学”;在现实中这类公民社会组成的行为体与主流理论研究中重视的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甚至跨国公司相比,也并不总在主流话语视阈内起到显著作用,这类行为体似是一个“被忽略的他者”。然而,这类力量真的被“忽略”了吗?本文认为,这支力量并未被忽略,而是被相对地隐匿了,其性质、手段与目的上的特征决定了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价值功用,同时也对国际实践产生了新影响。
其一,从性质上看,跨国倡议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仅具有相对独立性。诚然,跨国倡议网络通过各种手段对国家与其他行为体施压的行为有时的确促进了国际规范的迭代与演进,但囿于这类主体行为独立性的“残缺”,非政府组织有其金钱、雇员、组织机构、领导人、国际平台等物质性组成来源,在特定场域下难免存在偏离中立立场、自主性破碎的情形。[6]
其二,从其特定性质指引下的手段与目标来看,这类行为体的手段是激进的,而目的则是维护西方话语霸权。《活动家》中的多个案例皆表明:由多个非政府组织、媒体、部分知识分子和精英、甚至草根群体组成的看似无害、正面的“倡议网络”往往在话语与行为上过于激进,以“抗议性行为体(acteurs contestataires)”的身份出现。[7]然而,无论这类行为体通过何种手段与目的进行激烈的反抗或批驳,这种看似尖锐的“自我批评”运动,实则增强了主流理论体系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即通过一系列“理论折中”实现西方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的“桥接”,使代表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观念通过激进方式扩散至全球,最终增强西方话语霸权。[8]历史地看,各种“颜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多次表明西方长期以来通过此类行动的“民主”和“自由”等理念鼓吹国际关系民主化,实则旨在打造西式普世价值进路的意图。总的来看,这类群体实则始终皆“隐秘”而又“公开”地散布在全球各处并不时起着或建构或解构的重要作用,也自然就不完全是一个“被忽略的他者”。
其三,从非政府组织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上看,非政府组织的特定行为与英美等大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密切相关。美国大约有150万个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开展范围广泛的活动,包括对外交政策、选举、环境、医疗保健、妇女权利、经济发展和许多其他问题的政治宣传。他们的资金来源包括个人(美国或外国)的捐赠,私营部门的营利性公司、慈善基金会或联邦、州或地方政府的赠款。在白宫官网上赫然写着“美国坚信,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控制或政府参与——是民主繁荣的必要条件。”[9]不仅于此,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专设与非政府组织对接的部门,CARE、Save the Children US、Human Right Watch等非政府组织始终在美国的霸权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10]
在特定性质、手段与目标的指导下,跨国倡议网络等群体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倡议网络与非政府组织只能被资金更为雄厚、历史更为悠久、影响力更为巨大的西方倡议网络单方面地“代表”而难以阐述其真实诉求。[11]更有甚者,这招致众多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在现行联合国框架与国际法规约下逐渐改革与修正既有制度的同时,不得不被动地面临被跨国倡议网络、非政府组织无端“施压”“羞辱”的情形。跨国倡议网络囿于在地化融入的不足,有时反而是对实现更加公平合理国际秩序目标的背离,有时亦是一种过于规范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此,深入理解这类行为体的行为逻辑并妥善应对其带来的影响,是主权国家与政府间国际组织需要关注的事宜。
编:王叶湑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Tim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p. 405-425.
[2]玛莎·芬尼莫尔、凯瑟琳·辛金克:《国际规范的动力与政治变革》,载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魏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
[3]詹奕嘉:观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评《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4期,第117页。
[4]从主体上接续或扩展该领域的代表性研究参见刘莲莲著:《国际组织学:知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0版;William E. DeMars、Dennis Dijkzeul edited, The NGO Challeng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5; Molly A. Ruhlman, Who Participates in Global Governance? States, bureaucracies, and NGOs in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2015;从客体视角衍生的规范议程、规范属性研究可参见Amanda Murdie and David R. Davis, “Looking in the mirror: Comparing INGO networks across issue area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7, No. 2, 2012, pp. 177–202; R. Charli Carpenter, “Vetting the Advocacy Agenda: Network Centrality and the Paradox of Weapons Norm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1, 2011, pp. 69–102;从历时性上动态观察规范生命历程的研究可参见Amitav Acharya,“Whose Ideas Matter? Agency and Power in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Global Order: Agenc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5]例如,作者在全书第131页、183页一定程度地承认了因果机制相关性的限度,参见[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著:《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韩召颖、孙英丽译,第131页、第183页。
[6]可参见,Alexander Cooley and James Ron, “The NGO Scramble: Organizational Insecurit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national Ac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1, 2002, pp. 5–39; Emilie M. Hafner-Burton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Power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cial Networks,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1 ,2006, pp. 3–27; 徐莹:《残缺的独立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首要结构性困难解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3期,第108-112页。
[7]法国学者巴迪将反对既有国际体系并采取反抗策略的一类群体称作“抗议性行为体”以引出既有大国对“他者”利益与情感的漠视,参见[法]伯特兰·巴迪著:《世界不再只有“我们”:过于国际秩序的另类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宗华伟译,第13页。
[8]可参见张起著:《国际政治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2页。
[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 in the United States, FACT SHEET,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JANUARY 20, 2021,https://www.state.gov/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ngos-in-the-united-states/
[10] 此类非政府组织被学者称作“威尔逊式”非政府组织(Wilsonian NGO),意指该类行为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美国或特定国家对外战略服务的,独立性与中立性欠缺,与之对照的是更加独立、客观的“杜南特式”非政府组织(Dunantist NGO)。参见Abby Stoddard, Humanitarian Alert: NGO Information and its Impact on US Foreign Policy, Bloomfield: Kumarian Press, 2006, p. 15.
[11] 毕竟,拥有更强大物质性背景、更具有看似中立行为手段、更清晰、持续设立组织目标跨国倡议网络或非政府组织理所当然地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代表性文章参见George E. Mitchell and Sarah S. Stroup, “The reputations of NGOs: Peer evaluations of effectivenes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2, No. 3, 2017, pp. 397–419; Yoram Z. Haftel and Alexander Thompson, “The Independence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pt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0, No. 2, 2006, pp. 25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