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观察》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战略青年项目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新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经过编辑部评选,围绕热点问题撰写的优秀稿件将推荐至澎湃新闻等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转载。
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2篇书评,围绕约瑟夫·奈教授2020年出版的新书《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2022年中文译本)进行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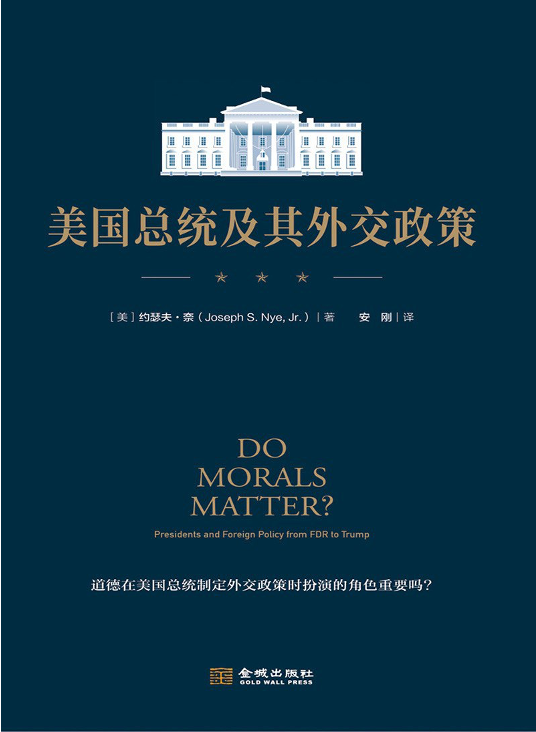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王静姝
《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2020年出版的著作。2022年金城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本(安刚译)译笔流畅,并配有大量详细的译注,清晰易读。约瑟夫·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长,后又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对美国外交政学界有多年观察和亲身参与。他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相互依赖论”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国际关系新自由主义理论,冷战后又创立“软实力”概念,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外交界均影响颇深。在本书中,作者基于对当前美国与国际秩序关系变化的关切,郑重提出了美国外交中的道德问题,从意图、手段和后果三个维度设计了美国总统的“道德记分卡”,对二战后十四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打分,以史论探讨美国未来的道德定位。
奈回应推崇传统权力政治者的观点,呼吁应重视道德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辩论并未停留在理论层面,奈躬行设计的美国总统“道德记分卡”成为本书一大亮点。结合历史的经验教训与21世纪的新变化,奈对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提出了大胆设想,重新定位自由主义,促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向更开放的方向改革;其主导者美国应正视国内政治极化对美国与世界互动的消极影响,以更宏阔的道德视野制定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外交战略。
一、挖掘外交政策背后的道德
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不同学科、不同立场的学者为其设计了五花八门的理论,包括战争与和平的正义问题、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全球分配问题等。奈讨论的层面属外交政策分析,也是道德讨论最薄弱的一环。由于本国利益是外交政策的基准,利他的伦理要求往往处于次要位置。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以道德原则约束斗争手段更易被视为作茧自缚。
因此,无论是霍布斯主义者还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都拒绝在外交政策中考虑道德因素。无视道德或许有助于在斗争中分析对手的真实意图,在极度对抗性的环境中求得自保,但历史比求生存更复杂,相比可比较计算的权力,道德以更隐蔽、弥散的形式影响着个人与集体行动,外交决策亦无例外。
奈清醒地指出,尽管在外交和战略决策中,道德因素往往不被彰显,但决策者事实上无时无刻不在做道德抉择。为理解隐含的道德因素,他基于在国际关系政学界的多年经验以及对道德哲学、伦理学的广泛涉猎,提出了理论框架,以“道德记分卡”的方式将政治领导人外交决策的道德分析可操作化。这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一大创举,能从历史中抽丝剥茧出隐含的道德元素,有助于我们更全面且深刻地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生成与演变。
二、辨识道德:从“道德记分卡”到“美德簿”
由于外交行动本身的公共性与战略性,对外交的道德评估不似传统伦理学的思维实验一般简单和瞬时。为回应这种复杂性,奈从意图、手段和结果三个维度提出了道德推理框架,并在标准制定方面寻求全面和平衡。与其说这是一份“道德记分卡”,不如说是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战略评估指南。如果说三个维度的区分提供了普遍的分析工具,那么各维度的评判标准则是奈集各家之大成列出的“美德簿”。从中可以厘出不同层次的价值,认识奈及其所代表的制度自由主义学派的价值立场,并辨析何者可推广而何者为美国之独特。
自由主义价值理想是奈“美德簿”的底色。在各个维度,对自由民主政治模式优越性的信念是无需思辨的背景,如奈在其他著作中所言:“美国自由民主的价值和程序”是他的规范性假设[1]。严格而论,美国总统发表的“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并非行事原则,只是一种想象的图景,应将其作为意识形态,与普遍外交行为中的美德区分开来。
不同于天真的自由主义者,奈的评判方式在自由主义的底版上镶嵌着现实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美德与原则。通过情境智力连接道德性与有效性,使其能与现实主义、世界主义者有效对话,并形成共识。奈接受了现实主义者强调的“审慎”(prudence)[2]这一美德并极力推崇。“审慎”代表了对代价和收益的谨慎权衡过程,判定代价和收益孰轻孰重背后则隐含了道德原则。奈最重视的道德原则是世界主义的人道原则,历史上美国总统为避免核战争、避免战事扩大、减少伤亡的努力获得了赞赏。面对这些抉择,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也要为人道原则让步,这与现实主义者也达成了一致。纵观奈对总统们的道德评分,个人德行也是道德评判的重要维度。当总统在外交政策中掺杂个人动机时,莽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当总统因私德不修、漠视国际制度或任意使用暴力而对公众和国际社会失信时,总统个人和美国的信誉将长期受损。
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理想、战略制定的品德以及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都融进奈的美德簿中。意识形态部分本属美国外交传统的一部分,但奈集各家观点的评述,仍可以帮助我们提取出各家公认的基本美德:因基本人道关怀的审慎、政治家的为公与守信。
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道德问题
在规范性之下,奈对二战后美国总统外交政策的评述也描绘了一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生成与演变史。延续威尔逊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战后初期的三位总统都走出了孤立主义,逐渐确立了美国的全球性外交政策。尽管威尔逊的遗产期待一个覆盖全球的制度体系,但自杜鲁门时期起,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过程与对苏遏制的目标密不可分。在冷战格局形成、白热化与瓦解的全过程,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介入 “往威尔逊的国际制度观里注入了现实主义因素”[3]。全球军事投射、兵不厌诈、软硬兼施,在不择手段的冷战对抗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成为一种阵营式秩序,并填充着暴力和威慑。
在此种秩序下,何言道德?鉴于以和平方式赢得冷战是美国的一大核心国家利益,奈大力赞赏卡特的人权外交。在人权法兴起的背景下,人权纳入外交工具结合了自由主义价值理想、强调规则与外交手段优先,完美契合制度自由主义对道德外交的设想。从后果来看,以话语取代武力、以外交手段平衡军事手段能减少伤亡,这也符合世界主义的人道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权外交为美国的价值理想提供了可行的工具时,美国特色的意识形态冲动便在道德推理中占了主导,其他更普遍的基本美德黯然失色。被工具化的价值不再关注人类而是服务于一国国家利益,便不具普遍道德意义。当奈称赞人权外交作为一种“软实力”促进了美国赢得冷战的国家利益并“促成了苏联的变化”[4]时,国家利益是他评判的主要标尺。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外交政策准星,这种扁平化的道德推理也导致了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崛起,美国破坏国际规范的冲动愈发无约束。道德征伐的消极后果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得不面对自身从冷战历史中继承的阵营化、意识形态化的封闭性。
四:想象新秩序:重新定位自由主义
可以把奈此时论述道德问题的努力看作制度自由主义者对美国过去外交政策中道德推理的回应。通过设计一个多层次、丰富的道德推理框架,奈既提醒新保守主义者看到更全面的美德集合,也在后冷战时代重新定位自由主义。回溯威尔逊自由主义的设想,奈将自由主义的内涵从自由民主的价值理想调整至国际制度与规则。他承认历史上美国总统都不是“完美的制度自由主义者”[5],违反规则的行为比比皆是。
如果说海外干涉、秘密行动甚至发动战争在奈眼中都只是少数特例,美国总统“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支持国际制度并寻求其进一步延伸的”[6],那么特朗普的“退群”“毁约”行为则是奈无法忍受的,他称这是一种“狭隘视野”,对规则和秩序持拒斥态度,并“依赖零和式的霍布斯现实主义”[7]。笔者以为,这也是奈在2020年急欲对美国人高呼“道德重要吗?”的核心关切。自由主义者可以接受以道德为名的秘密海外行动,但若美国走向孤立的、不与国际机制接触的方向,自由主义的价值理想将再无实现可能。美国回归国际机制是奈想象新秩序的第一步。
回归并非复原一个美国主导的、不愿卸下冷战包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人们因国家力量消长而焦虑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被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遭挑战时,他们将制度和秩序理解为一个完整不变的体系,与有权势者捆绑,被有权势者塑造、主导甚至成为其所有物。但制度与秩序是各主体互动的结果,他者一直存在,他们与有权势者一样有对世界的道德关怀,希望也应当被看见并被尊重。
与权力转移、霸权更迭等论调不同,奈选择反思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试图超越自由主义理想作为意识形态的狭隘性。在他的“道德记分卡”中,他巧妙地将“自由主义”标识为尊重制度而非某种意识形态冲动。通过将“自由主义”的概念改换为制度合作的手段,奈悬置了威尔逊以来美国人期待的自由主义理想:即世界遍布美式自由民主国家。这一悬置意识形态的做法并非第一次,但对赢得冷战后沉溺于霸权幻象并因此焦虑的美国来说,这是值得一试的药方。隐去“自由主义”这一附着太多意识形态的元素,一个开放的国际秩序将有可能。承认不同政权性质的国家可以共存并为了共同目标合作,将是全球化时代之最大道德。
当然,奈从未放弃基于美国价值观的软实力,他理想的目标是部分权力共享的同时美国继续保持权力凌驾。他期待合作与和平,提出“长期多元化”的设想,但并未推展至永久。在世界各地新保守主义、本土主义声音渐强的今天,我们不清楚美国能否安然接受与他者共存,也不清楚世界能否平稳地走向多元共存。但至少我们仍可以脚踏实地,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探索可能的正和互动。
编:刘宇宁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Jr, Nye, Power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Age: From Realism to Globalization,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18.
[2]“审慎”(prudence)与节制、适度相关,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源远流长的概念。在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尼布尔、摩根索等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审慎是国际政治的道德核心。奈并未否定现实主义学派的审慎原则,他与现实主义学派的区别在于:希望从其他视角扩展国际政治的道德内涵,审慎仅作为其中之一而非核心。关于审慎原则在政治思想史的探讨,可参见左希迎,刘丰:《国际政治中的审慎原则——思想源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3]约瑟夫·奈著,安刚译:《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北京:金城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4]同上书,第137页。
[5]同上书,第227页。
[6]同上。
[7]同上书,第2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