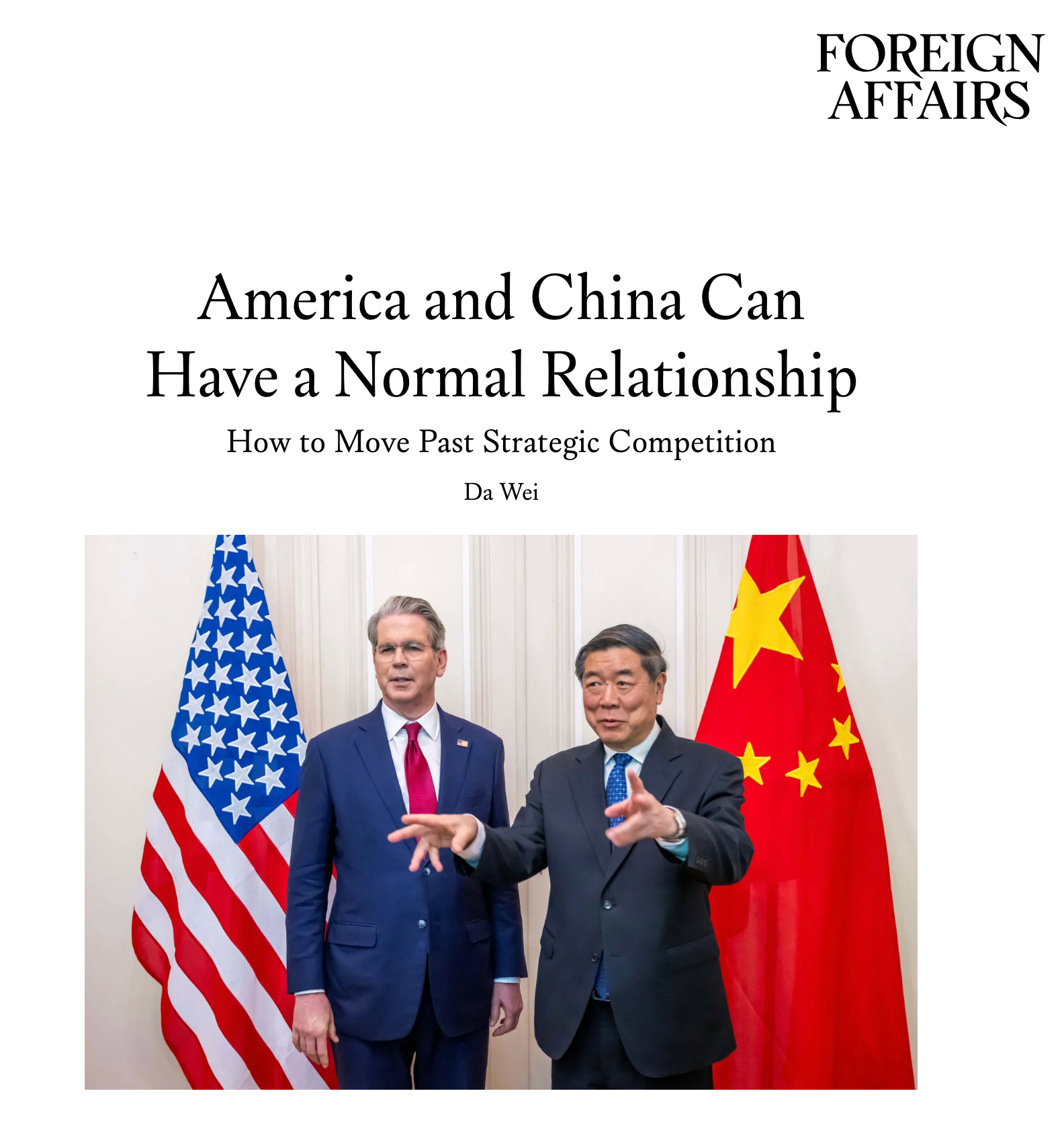
在一再重复的中美对抗与缓和的循环中,一种矛盾的现象正在浮现。一方面,中美经济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张:10月上旬,美国和中国在短短的六个月内第二次濒临贸易战,双方都准备实施严厉的出口管制,并威胁将自对方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却也显现出更强的韧性。尽管华盛顿和北京似乎都对全球两大经济体的脱钩趋势显得无能为力,但4月至5月的贸易摩擦最终让位于一段相对的平静期。在过去十个月中,乃至拜登政府的最后两年里,中美关系都在出现再平衡的迹象。每当危机爆发,例如2023年的无人飞艇事件之后,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会迅速寻求稳定局势——这说明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仍然在结构性上需要一种总体稳定的关系。
中美关系或许正处在一个转折点。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都不再幻想两国能回到2017年前以“相互依存”与“接触”为特征的旧时代。然而,短期的经济摩擦与策略性博弈不应掩盖这样一种可能:美国与中国完全可以超越敌对竞争的阶段,建立一种更为“正常”的关系,一种冷而不僵、竞争但可共处的关系。本周在韩国举行的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将给中美关系提供一个虽窄却关键的契机,使其进入新的阶段。
美国vs.全世界
转折点的出现,部分源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在北京看来,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标志着战略竞争时期的开始。彼时,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对手与竞争者,核心目标是遏制和减缓中国的经济与技术崛起。换言之,那是“美国vs.中国”的时期。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目标,但更倾向于通过联合盟友来实现,这一阶段可以被称为“西方vs.中国”的时期。中国战略界普遍认为, 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两人都认定中美利益根本对立,因此唯一的选项便是毫不妥协的斗争,几乎没有妥协空间。
尽管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继续向中国施压,但美国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再平衡。特朗普正在重新调整美国与世界的经济与安全关系。其4月2日宣布的所谓“解放日关税”波及百余国,包括许多盟友。特朗普政府反复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即便因此损害传统关系也在所不惜。如今,美国的做法不再是“美国及其盟友vs.中国”,而更接近于“美国vs.世界其他国家”。
历史上,中美总是拥有一个整体性的合作基础。由于有这个基础,具体分歧就相对容易管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美两国联手应对苏联威胁;冷战结束后,两国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并共享收益。但在过去十年,随着各国逐渐远离全球化,中美合作的根基不断削弱。如今,特朗普政府几乎完全否定旧的全球化模式,并将外交重点从“针对中国”转向“重塑对所有国家的政策”,这反而为中美关系建立新的基础创造了机会。
全球化之后
无论华盛顿还是北京的战略家与决策者,往往都将过去十年中美关系的恶化归咎于对方的敌意政策。但另一种解释是——旧的全球化模式本身已无法为继。两国关系的恶化,更多地是结构性转变的结果,而非相反。
在美国主导的冷战后自由国际秩序中,中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然而,中国以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模式崛起,这事实上将自由主义秩序撑薄到了其极限。与此同时,美国虽也从单极自由体系中获益颇丰,却未能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全球化给其国内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失衡,最终引发了强烈的内部反弹。
今天,美国正在拆解自己曾经主导的体系。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力量都在背离自由国际主义,转而拥抱产业政策与经济民族主义。如今的中美两国都不再单纯为了追求经济效率而接受对对方金融体系、关键产品与先进技术的无条件依赖。去全球化的进程已无法阻止,各国只能学会适应。
中国的自信心的上升或许也有助于适应这一变化。尽管美国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中国半导体等产业的发展,中国仍在持续实现技术突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仍保持增长态势;同时,北京也找到反制手段,如管控稀土磁体出口,从而影响美国关键产业。自信的中国更可能将关注重点放在国内稳健的经济政策上,而非过度忧虑外部压力。未来,中国不仅能继续发展前行,而且其在全球相较于美国的地位还可能得到进一步提高。
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的决策者迎来了罕见的“降温”机会。北京可重新审视:美国是否真的是一心地要阻止中国崛起?华盛顿也可反思:中国是否真意在颠覆美国领导的秩序?这种叙事上的调整,有助于两国摆脱敌意,从而恢复更具建设性的互动。
再平衡的路径
美国与中国不必成为朋友,但必须避免成为敌人。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意味着重新平衡两国的相互依存方式。
几十年来,中美经济联系实际上是高度不对称的:中国依赖美国的金融体系与高科技以支撑发展,而美国则依赖中国制造业提供廉价消费品。过去十年中美之间的激烈竞争打破了这种旧格局。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美国不再容忍对华巨额贸易逆差;而中国也对于依赖美国金融与技术优势十分警惕。实际上,早在2018年贸易战爆发前,两国已开始在部分领域“脱钩”。
在一种正常的稳定关系中,中美竞争仍将存在,但其强度需要得到控制。两国应明确哪些领域可以互动、哪些领域应保持独立。中国在电动车与电池制造等领域对美投资,可在产业、技术与金融层面分别形成更平衡的中美相互依存;当然,这种合作只能在双方同意的特定领域进行。这种相互依存更稳固、更可持续,也更容易让双方都感到“受益公平”,并更愿意维持这种平衡。
在地缘政治层面,两国也需重新校准。美国军方频繁在中国沿海进行抵近侦察与所谓“航行自由行动”,强调其合法权利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但这些行动实际上极易引发两大军事强国的危险摩擦。美国可通过减少挑衅性活动、利用其他技术手段替代侦察任务,降低军事对抗风险,同时仍能让美国维持其对盟友的承诺。
两国领导人还可在台湾问题上缓和紧张。特朗普政府若能正式重申反对“台独”,将向北京传递关键信号。作为回应,北京可努力减少台海军事紧张并扩大两岸交流。只要北京相信和平统一仍有希望,动武的紧迫性就会下降。这种安排与特朗普“调停长期冲突地区”的全球愿景是一致的。
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总是强调普世使命,而中国则专注国家建设。如今,中美关系首次成为两个民族主义大国的关系:特朗普总统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习主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实都是民族主义目标,二者并非必然对立。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全,或至少互不妨碍。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也表明,当美国的外交更聚焦于自身时,它往往对中国更为克制,例如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美国在南海的行动明显降温。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无法真正削弱对方的经济,但如果敌对竞争持续失控,双方仍有足够手段给对方造成实质性损害。随着特朗普总统与习主席在韩国重启谈判,中美关系的确具备双边关系再平衡的可能。这一转折并非必然,但它是可能的,也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