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课题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六次会议(COP26会议)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气候变化(以下简称“气变”)[1]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背景下,气变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加病毒扩散风险,威胁公共健康。[2]气变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欧盟和以美国为首的伞形国家集团是影响气变进程的重要政治力量。在新形势下,研究美欧气变政策的特点、分歧及前景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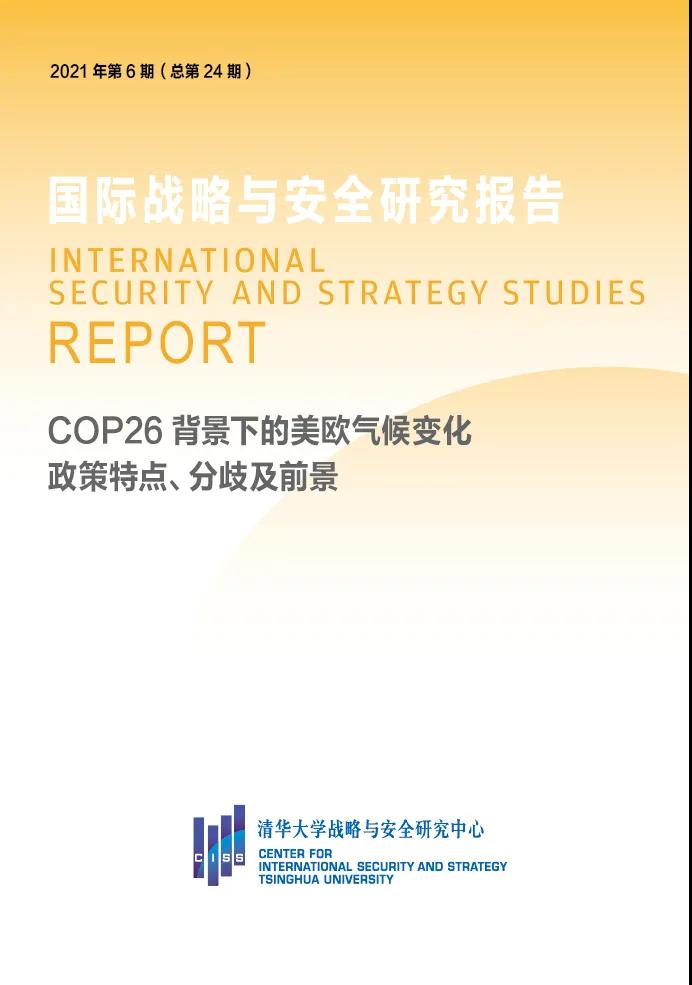
一、美欧气变政策特点
美国与欧盟是全球关键的两支力量,双方都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健全的国内环保法规,参与并影响国际气候双边与多边制度和国际气候合作。以COP26为契机,美欧在今年都提出了自己的倡议,力争掌握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美方4月承诺,到2030年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2005年的50%-52%,还在本次气候大会宣布价值30亿美元的总统“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Emergency Plan for Adaptation and Resilience)以提升气候宣传、融资和适应能力。欧盟4月制定“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战略目标并于7月正式提出“2035年起禁止出售汽油及柴油车辆,推动零排放电动汽车的普及”。受诸多因素影响,双方的气变政策各有特点。
(一)冷战后美国气变政策经历六届政府的演变,其整体特点为实用主义、单边色彩、摇摆不定。美国气候外交政策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更多从国际战略意图出发,并且顺从国内政党政治,而不完全是所谓的“全球气候环境责任”。拜登执政后,美国的气变政策表现出政府积极、州内踊跃(以加州最明显)、党内贯彻“绿色”理念的特点。拜登气候政策的调整事关美国环境利益和国际形象,尤其是面临中期选举压力的拜登更不愿将气候主导权拱手让给欧盟和中国,希望“以外促内”,利用气候治理为民主党的执政加分。
总体而言,拜登政府的气候治理政策可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考察。国内层面上,拜登提出“中产阶级外交”,结合竞选期间“绿色新政”[3]的相关倡议,试图将应对气变与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转型、建设基础设施等国内要务结合,并努力推动国会通过包含一系列气候治理内容的支出法案。
国际层面上,拜登政府将气变议题打造为美国重返多边主义、重塑盟友关系、重夺世界事务领导地位的抓手。一是将气候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推动一系列倡议和举措。拜登在竞选期间就提出,美国不仅将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还将不遗余力运用外交手段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气变威胁。国务卿布林肯也明确强调,美国将把气候危机置于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中心。[4]二是将气候外交作为美国重返世界舞台的主要措施之一,强化美国在这一议题上的“领导形象”。双边领域,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拜登执政百日之内就相继出访欧洲与亚洲,尤其是在访华期间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会谈,达成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5]此后,克里又陆续访问多个国家,展开气变领域的“穿梭外交”。多边领域,拜登希望扭转前任政府在气变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努力重夺在该议题上的引领权。
(二)欧盟的气候政策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前瞻性,但欧盟内部的利益分歧也导致其气候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加复杂化。在应对气变问题上,欧盟起步早、目标宏大,其成员国相继签署了一系列重大减碳降碳协议,但是在具体措施方面却存在巨大差异。从欧盟内部看,成员国在气变问题上存在“领先国”与“滞后国”之分。[6]这种差异与分化给欧盟气候政策和气候外交带来重大影响。“领先国”与“滞后国”的矛盾在于,“滞后国”为了本国经济利益不愿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政策,且气候问题在国内不占据中心地位;而“领先国”积极促使欧盟实施共同的气候政策,不仅因为希望欧盟区内形成良好的生存环境,还因为担心其他成员国的消极政策损害自身在统一大市场内的竞争力,其考虑是更严格的环保标准会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因此,欧盟的共同气候政策取决于“领先国”与“滞后国”之间的利益协调。此外,欧盟气变提案还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在工业、地理、能源供应和投资能力方面的情况大不相同,对化石能源依赖程度也不同。各个产业和利益集团的游说使得相关谈判工作步履维艰。10月21日,COP26大量机密文件的泄露也说明了这一点。[7]
国际层面上,欧盟在全球应对气变问题上力求掌握领导权的意图和举措愈加清晰。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之后,欧盟也积极部署生态地缘战略以弥补欧盟在气候环境外交政策层面上的不足。欧盟还将气候政策与冲突解决纳入欧盟防务政策路线图。[8]同时,欧盟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积极推行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综合战略并加大绿色投资。
二、美欧气变政策分歧
在气变问题上,即使是以美欧为主体的西方内部也存在明显分歧。美欧是较早重视并投身气变治理的国际参与方,对于全球气变治理发挥重要作用。此前,特朗普政府悍然退出《巴黎协定》,严重冲击气变治理,标志着美欧出现前所未有的分歧,而拜登执政也并不意味着美欧气变政策分歧就此弥合。双方政策分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对全球气变治理的推进基础、治理偏好和治理规则的认知差异显著。欧盟长期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机构的气变科学评估报告作为其全球气候和减排主张的基础。欧盟社会普遍认为气变是重要威胁,应对气变在欧洲已成为普遍的“政治正确”。欧盟民众、企业、非政府组织及欧盟内部各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应对气变危机。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气变并未形成统一的科学共识和政治认知。英国民调机构舆观(YouGov)的数据显示,美国民众中气变怀疑者的比例居全球之首,这种认知影响美国政府的国际气变谈判立场。
(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气变政策的目标制定上,欧盟自《京都议定书》后就以争当气变领域“领军者”为己任,不仅注重将自身的国际承诺转化为每个成员国的减排责任,更重视对其他国家的“示范与引领”作用。而美国却在“目标引领”上态度消极,抵制率先减排或提出超越现有发展阶段的减排目标,并把发展中国家负担相应责任与美国设定减排目标挂钩。小布什政府2001年宣布放弃实施《京都议定书》和特朗普政府2017年单方面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举措,均反映了美国的这种心态。“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美国一直坚持将2005年作为气候治理目标的基准点而非欧盟强调的1990年,以保证在1990-2005年间拥有更多的碳排放权,进而保护经济发展利益。[9]
欧盟在气变政策上注重通过内部立法和政策制定来落实国际气候承诺,制定并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碳排放交易体系、电力市场、运输行业等领域的内部指令,以提升欧盟气候目标和承诺的落实成效。美国的三权分立、两党政治等因素都将掣肘其在国内落实气候治理政策的力度和广度,因而其承诺的可信度引发包括欧洲在内的国际社会多方质疑。克林顿和奥巴马两届民主党政府均因难以通过国内立法程序而只以总统个人名义签署国际气候协定。拜登此次参加COP26之前也未能推动国会通过包含气候治理在内的社会支出法案。
(三)欧盟对发展中国家气候援助力度远超美国。欧盟不仅以自身不断提升气候承诺向发展中国家“示范”,而且也通过发展援助、伙伴关系、自贸安排等政策与气候外交相结合,共同推动发展中国家增加对气候治理的贡献。而美国则长期将发展中国家是否参与减排与本国减排挂钩。克林顿政府因发展中国家缺乏减排安排而拒绝落实自身承诺,特朗普政府更是将气变称之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阴谋”并退出《巴黎协定》。[10]拜登执政后虽重返《巴黎协定》、签署气候行政令,但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施压并未减少。
三、前景
合作与分歧并存是美欧气变政策互动的常态,但“特朗普式”的气变政策对于美欧盟友关系和全球气候治理进程都造成了重大破坏。展望未来,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在气变构想及政策上的合作阻力仍将主要源于内部分歧,例如美国的两党政治极化、特朗普的“政治遗产”、社会共识的缺乏以及国内捉襟见肘的财力。
从美国方面看,拜登执政以来在气候领域通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和政策宣示,向国内及国际社会明确传达“美国回来了”的决心。然而,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施政目标仍需要经过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层层考验,最终能否细化落实为明确的政策实绩,并通过长期和稳定的政策设计确保最终实现,尚待观察。气候议题上两党的政治极化将继续阻碍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推进。气候行政令的推行还将受到司法层面的挑战,最高法院在美国的气候政策中扮演了被动参与者的角色。法院虽然不能主动干预国家政策,但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发起诉讼的方式,要求法院对政府的环境政策进行复审。特朗普执政期间总共任命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使保守-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达到6-3,这一“政治遗产”将使拜登政府行政令的推行面临更大阻碍。美国国内反对气候治理的政治杂音也将成为拜登政府气候政策必须面对的难题。
从欧盟方面看,气候政策最大的挑战源于欧盟“领先国”与“滞后国”之间经济利益分歧造成的减排立场差异。“领先国”担心自己的竞争优势下降,认为欧盟气变目标过于激进、反对严格的减排措施。此外,今年二季度以来,供给问题还引发了欧洲能源危机。2015年以来欧洲天然气生产规模呈现逐渐下降趋势,2020年以来尤为明显,能源供给形势更加严峻。因此,欧盟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也面临较大的成本约束,将阻碍其推进气候治理政策的实施。
尽管如此,美欧在促进全球经济结构转向更清洁、低碳和环境友好模式上有着共同利益。美欧双方在气变领域可携手合作,也可发挥示范作用,并推进主要碳排放国通过气变合作共同构建全球低碳叙事的潮流。美欧为提升气变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客观上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推动力,也为中美、中欧乃至中美欧开展相关合作提供了契机。11月10日,中美两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格拉斯哥大会期间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并同意建立“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推动两国气变合作和多边进程。
然而,美欧却在可能有损自身经济发展利益的方面向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欠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承诺施压”和转嫁历史环境责任,从而导致欠发达国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碳约束”的挑战。同时,美欧能源和经济禀赋、产业利益格局差异以及在绿色金融、低碳产业等方面的竞争关系,也将使得气候领域的具体合作议程和公众共识因利益产生分歧,进而直接影响气候政策的落实前景。
文内注释
[1] 不同资料中出现的“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气候变暖” (Climate Warming),“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在本报告中, 三者的含义等同且统一为“气候变化”并简称为“气变”。
[2] 《报告:气候变化或增加病毒扩散风险 须引起高度警惕》,《中国气候变化信息网》,2020年11月30日,http://www.ccchina.org.cn/Detail.aspx?newsId=73410&TId=62%22%20title=%22%E6%8A%A5%E5%91%8A%EF%BC%9A%E6%B0%94%E5%80%99%E5%8F%98%E5%8C%96%E6%88%96%E5%A2%9E%E5%8A%A0%E7%97%85%E6%AF%92%E6%89%A9%E6%95%A3%E9%A3%8E%E9%99%A9%20%E9%A1%BB%E5%BC%95%E8%B5%B7%E9%AB%98%E5%BA%A6%E8%AD%A6%E6%83%95
[3] 拜登提出以“绿色新政”作为解决气候变化的关键框架,重点政策目标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在2050年前实现100%清洁能源经济与净零排放,推动建立相关执法机制以实现净零排放;第二,提升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第三,将气候变化打造为国家安全核心优先事项;第四,反对损害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社区的环境污染者,通过全政府的方式推动“环境正义”;第五,履行对工人和社区的义务,尤其是受到能源转型影响的工人。参阅, BIDEN HARRIS DEMOCRATS, “THE BIDEN PLAN FOR A CLEAN ENERGY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https://joebiden.com/climate-plan/
[4] Antony Blinken, “Tackling the Crisis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merica’s Global Climate Leadership,” April 19,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remarks-to-the-chesapeake-bay-foundation-tackling-the-crisis-and-seizing-the-opportunity-americas-global-climate-leadership/
[5] “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全文)”, 新华网,2021年4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4/18/c_1127342714.htm
[6] “领先国”是指那些国内政治受绿党和环保组织影响较大、国内环保法规比欧盟法规相对更加严格的国家,它们往往在欧盟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环保政策向前发展,其代表是德国、丹麦、荷兰等国:“滞后国”则是指那些环境措施相对较弱、不太情愿接受更严格的环保措施、基本上按照欧盟环境法规实行国内环境立法的国家,主要指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比利时等国。
[7] 西方国家正试图改变一份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科学报告,欧盟在内的国家要求联合国淡化化石燃料对气变的重要影响。德国是欧盟内工业和制造业实力最强的国家,对气候政策非常敏感。德国政府认为气候保护不应危及工业竞争力,必须避免因气候政策过于严苛而导致工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现象发生。详见, Justin Rowlatt & Tom Gerken, “COP26: Document leak reveals nations lobbying to change key climate report", BBC. News. October 21,2021.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8982445
[8] Richard Youngs, “COP26 and the Foreign Policy Blind Spot in Europe’s Climate Action. Judy Dempsey’s Strategic Europe,” October 26, 2021 https://carnegieeurope.eu/strategiceurope/85648
[9] 美国曾在《京都议定书》签字,但并未送交参议院进行批准程序。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原则上并不反对《京都议定书》的思想,但是他认为议定书规定的要求太高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参阅:David Corn. George W. Bush: The Unscience Guy, 2001-06-19
[10] 参阅:董一凡、孙成昊:《美欧气候变化政策差异与合作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104-108页。
撰稿:刘宇宁(外交学院博士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美欧研究项目”青年研究员)、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